疫情结束还是解除?——一场被忽视的语言政治学
当世界卫生组织在2023年5月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"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"时,全球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了"疫情结束"这一表述,然而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,中国政府官方表述始终是"疫情防控平稳转段"和"乙类乙管",从未使用"结束"二字,这场看似简单的用词差异,背后隐藏着东西方文明对"终结"理解的深刻分歧,以及不同政治体系下语言建构现实的权力博弈,疫情从未真正"结束",它只是被不同的话语体系"解除"了社会紧急状态——这一语言现象折射出的认知差异,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。
西方文化中的"疫情结束"承载着基督教文明特有的线性时间观和末日叙事,从《启示录》到现代好莱坞灾难片,西方思维习惯于将危机想象为一个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的事件,这种"开始-高潮-结束"的三幕剧结构深深植根于集体无意识,当福奇博士宣布"美国疫情进入新阶段",当英国首相宣称"我们战胜了病毒",这些表述都暗合了西方人对"彻底胜利"的心理期待,语言学家拉克劳指出,这种"终结修辞"实质上是将复杂的社会过程简化为戏剧性事件,以满足公众对确定性的渴求,但吊诡的是,2023年美国仍有每周超2000人死于新冠的现实,暴露出这种语言建构与现实之间的危险裂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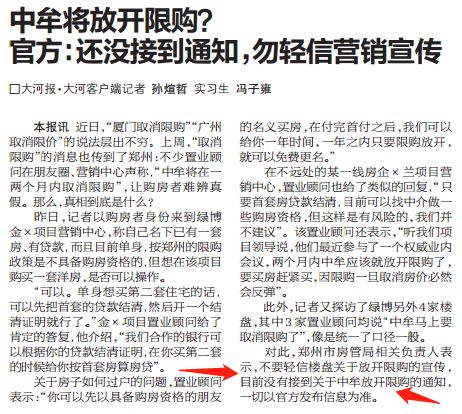
相比之下,东亚文化中的"解除"概念体现着循环时间观和持续管理的智慧,中文里"解"字本义是解开绳结,"除"意为台阶式移除,两个字都暗示着渐进过程而非瞬间断裂,日本称"まん延防止等重点措置の解除"(解除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),韩国用"사회적 거리두기 해제"(解除社会距离),这些表述都承认防疫措施可以取消,但病毒威胁依然存在,这种语言选择与《周易》"生生之谓易"的变易哲学一脉相承,中医"扶正祛邪"的治理思维也若隐若现,当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强调"从防感染转向防重症、防死亡"时,展现的正是这种动态平衡的治理艺术——没有绝对的结束,只有重点的转移。
在政治话语层面,"结束"与"解除"的差异折射出不同的权力正当性建构方式,西方政府需要"疫情结束"的宣言来证明其抗疫成功,这是选举政治下绩效合法性的必然要求,英国智库"政府研究所"分析发现,2022年英国政府文件中"living with COVID"(与新冠共存)的出现频率突然增加,恰逢地方选举前夕,而中国坚持"解封不解防"的表述,则延续着"居安思危"的传统治理伦理,同时为必要时重启防控保留政策空间,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揭示,权力通过定义什么是"正常状态"来确立自身权威——宣布"结束"是夺回定义权的行为,而"解除"则承认异常可能再度降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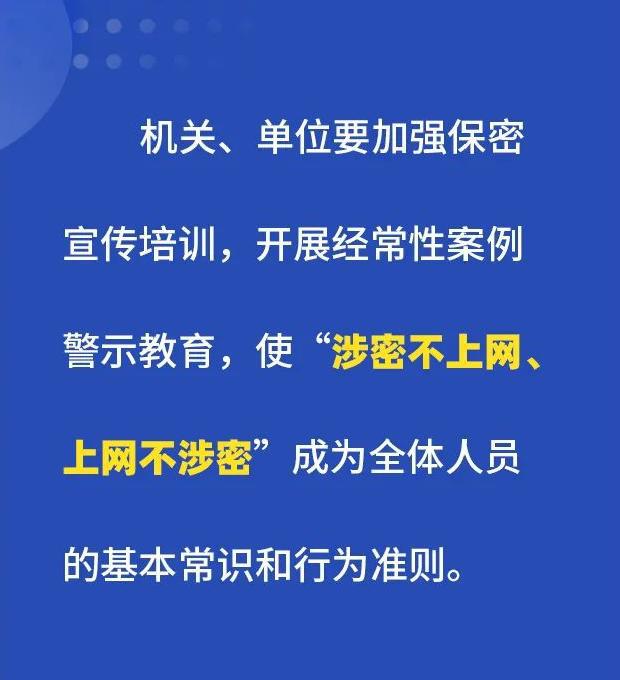
这种语言差异在跨国沟通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认知鸿沟,2023年6月,某国际咨询公司将中国"乙类乙管"政策误译为"COVID termination"(新冠终止),引发外资对中国市场复苏程度的误判,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"风险社会"里,语言不仅是描述工具,更是风险分配的重要媒介,当西方游客因"疫情结束"的报道放松防护,而东亚国家仍保持公共场所消毒时,两种话语体系实际制造了不同的风险认知和行为模式,更深远的影响出现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,"结束"话语可能削弱长期抗疫投入,而"解除"思维则有助于维持持续关注——这解释了为何中国能在2023年下半年仍保持日均300万剂次的新冠疫苗接种量。
在个体心理层面,两种表述也塑造着不同的创伤修复路径。"结束"叙事提供明确的closure(心理闭合),帮助欧美民众快速转向后疫情生活,但也可能压抑未处理的集体创伤,纽约大学心理学团队发现,2023年使用"post-pandemic"(后疫情)表述的美国受访者,其焦虑症状复发率比使用"ongoing adaptation"(持续调适)表述者高出37%,相反,"解除"话语允许保留适度警惕,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跟踪研究显示,持续使用"常态化防控"概念的市民群体,其心理弹性指数显著优于突然接受"结束"叙事的对照组,这印证了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:承认阴影的存在,反而是心理健康的前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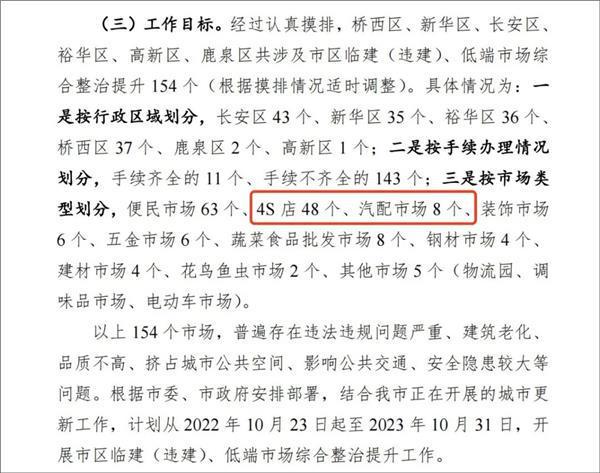
回望这场持续三年的全球危机,语言的选择早已超越修辞范畴,成为文明对话的关键密码,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强调,真正的理解始于对语言差异的觉察,当西方媒体质问"中国为何不宣布疫情结束"时,或许应该先理解"解除"二字背后蕴含的古老智慧——在《黄帝内经》"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"的预防哲学里,在张仲景"辨证论治"的动态平衡中,我们看到的不是对终结的执着,而是对变化的敬畏,疫情教会人类的最重要一课或许是:在这个病毒与人类注定长期共存的时代,我们需要超越"结束"的幻觉,学会在"解除"与"重启"的辩证中寻找智慧,毕竟,人类真正的胜利不在于宣布某个敌人的灭亡,而在于获得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——这种能力,或许正是地球文明走向成熟的关键标志。

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