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的断层,我们为何对疫情元年的确切日期如此模糊?
2020年1月20日,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,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,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、控制措施,这一天,后来被公认为中国新冠疫情正式爆发的标志性时间节点,然而有趣的是,当我们询问普通人"疫情是哪年几月几日开始的"时,大多数人会陷入迟疑和不确定,这种集体记忆的模糊性,折射出人类面对重大历史事件时独特的心理防御机制和认知特点。
一、历史性时刻的悖论:为何重要日期反而难以记住?
心理学研究表明,人类大脑并非简单的信息存储设备,而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信息处理系统,对于新冠疫情这样具有创伤性的事件,我们的记忆往往呈现出"宏观清晰,微观模糊"的特征,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·夏克特的研究指出,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记忆会形成"闪光灯记忆"——人们能清晰记得自己当时在做什么、感受如何,但对具体日期却常常混淆。
这种记忆特点在历史事件中屡见不鲜,比如很少有人能准确说出2001年"9·11"事件的具体星期几,尽管每个人都记得那是9月11日,同样,对于2008年汶川地震,大多数人记得是5月12日,但具体时间点却存在记忆偏差,疫情日期的模糊性,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心理对创伤性事件的自我保护——我们记住事件的影响,却有意淡化其精确的时间坐标,以此减轻心理负担。
二、疫情时间线的科学重构:从模糊到精确
医学史视角下,新冠疫情的时间线其实相当清晰,2019年12月1日,武汉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;12月31日,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;2020年1月7日,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首株新冠病毒毒株;1月20日,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冠病毒"人传人";1月23日,武汉"封城",这一系列精确到日的时间节点,构成了疫情初期的科学时间轴。
公众认知与科学记录之间存在明显鸿沟,英国《自然》杂志2021年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,仅有17%的受访者能准确说出本国疫情开始的关键日期,这种差异揭示了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的"时间压缩"现象——公众倾向于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单一象征性时刻,在中国语境下,1月23日武汉"封城"往往被视为更具象征意义的"疫情开始日",因为它标志着抗疫措施的重大升级,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三、数字时代的记忆悖论:信息过载与记忆消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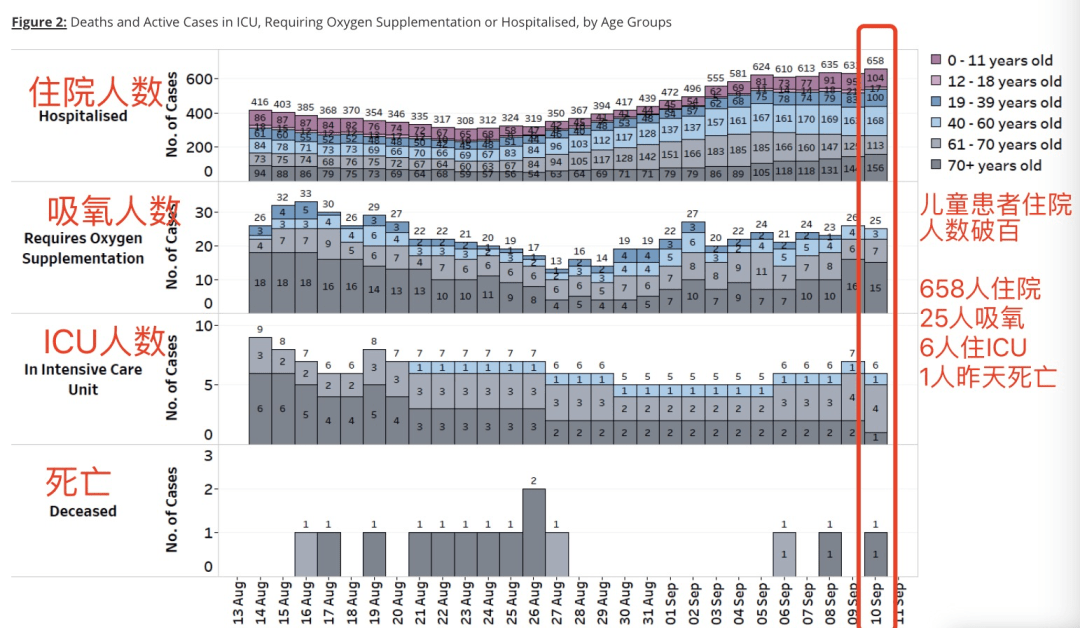
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,我们面临一个奇特悖论:记录工具日益精确,集体记忆却愈发模糊,社交媒体上每天海量的疫情信息,反而造成了记忆的"过载效应",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研究所的神经科学研究显示,当信息输入超过大脑处理能力时,人类会启动"选择性遗忘"机制,优先保留情感体验而非具体数据。
疫情期间,我们见证了这种记忆机制的典型表现,人们清楚记得口罩短缺的焦虑、居家隔离的无聊、健康码带来的不便,却难以记起这些变化发生的具体时间点,法国哲学家保罗·利科所称的"叙事性记忆"在此发挥作用——我们更倾向于以故事形式记住事件,而非冷冰冰的时间序列,这也解释了为何"武汉封城"这一戏剧性事件比卫健委公告更容易被记住。
四、全球化视角下的"疫情元年":不同国家的时间认知差异
新冠疫情作为全球性事件,各国对其开始时间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,意大利将2020年2月21日伦巴第大区爆发视为本国疫情起点;美国则以2020年1月21日华盛顿州首例确诊为标志;韩国将2020年1月20日首例输入病例作为开端,这种差异导致"疫情元年"在全球集体记忆中的碎片化。
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吉尔·莱波雷指出,这种时间认知差异反映了各国抗疫叙事的建构过程,中国将抗疫塑造为"人民战争"叙事,因此强调国家层面的响应时间;意大利注重医疗体系崩溃的创伤记忆;美国则突出联邦与州政府间的应对矛盾,每种叙事都选择了不同的时间节点作为象征性起点,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对疫情开始时间的认知分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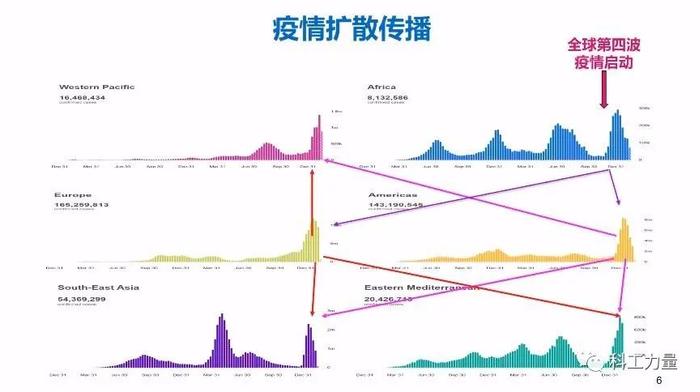
五、记忆政治学:谁在定义我们的"疫情元年"?
疫情时间的界定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纪年问题,而是涉及深层的记忆政治,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·哈布瓦赫的"集体记忆"理论认为,社会主导群体会通过控制重大事件的时间界定来塑造历史叙事,在中国语境下,1月20日作为官方确认"人传人"的日期,具有制度性记忆的特征;而民间更记忆深刻的1月23日"封城",则代表了社会性记忆。
这种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的微妙差异,在各国抗疫叙事中都有体现,日本学者大泽真幸研究发现,日本民众对2020年4月7日"紧急事态宣言"的记忆强度,远超过1月16日首例确诊的官方日期,这种记忆分化反映了民众更关注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政策措施,而非单纯的疫情开端。
六、后疫情时代的记忆重构:从精确日期到文化符号
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,人们对"疫情元年"的记忆正在经历符号化转变,就像我们不再追问"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几点开始"一样,新冠疫情的具体日期也将逐渐让位于更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记忆符号,意大利已经将"2020年春天"整体作为文化记忆单元;中国则形成了"那个春节"的特指表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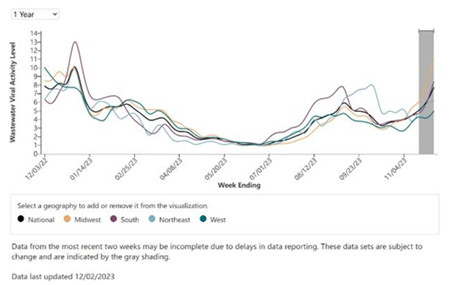
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·霍布斯鲍姆所说的"发明的传统"正在疫情记忆中形成,我们创造新的时间表述方式——"前疫情时代"、"疫情高峰期"、"后疫情时代",用这些模糊的时间概念替代精确日期,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框架,这种记忆转型不是历史精确性的丧失,而是人类适应重大创伤的心理调适过程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:"疫情是哪年几月几日开始的?"我们发现,这个看似简单的时间询问,实则揭示了人类记忆机制的复杂性,2020年1月20日作为中国疫情爆发的关键节点,其历史意义不会因公众记忆的模糊而减弱,相反,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成为疫情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它告诉我们,重大历史事件在集体记忆中存活的方式,从来不是冰冷的时间数据,而是交织着情感体验、文化符号和社会叙事的复杂网络。
在记忆的断层处,我们反而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——一个不完美但充满适应力的物种,用独特的方式处理着共同经历的创伤与成长,也许,对"疫情元年"日期的集体模糊,恰恰是人类心理韧性的最好证明。





发表评论